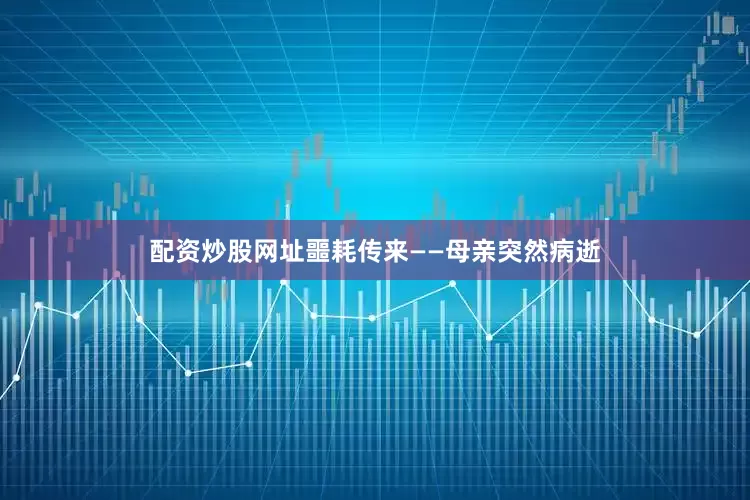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闻玉梅,已近九十高龄,却依然精神焕发,步履矫健。她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特别的画作:在茫茫的雪地里,几朵红梅傲然绽放,那正是她的堂兄闻一多先生之子闻立鹏特意为她绘制的作品。闻玉梅常说:“那梅花纯白如玉,火红似火,就像我人生的追求。”即便年事已高,她依然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,坚守着初心。“我永远铭记自己是国家人才培养的对象。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,我都不会放弃追求。只要我还健在,思维清晰,我必将继续未完成的科研,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”
1930年,一对年轻夫妇双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,携手回到了祖国。丈夫闻亦传是闻一多先生的堂兄,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;妻子桂质良则专注于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研究,是我国首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。1934年1月的寒冬,梅花如约盛开,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女儿,取名闻玉梅。家中两个女儿健康成长,小家庭洋溢着幸福与欢笑。然而命运无情,闻亦传因肺结核英年早逝,年仅五岁的闻玉梅便经历了失去父亲的痛苦。
两年后,闻玉梅跟随母亲来到上海。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,桂质良兼职多份工作,日夜奔波劳累。尽管如此,她依旧忧国忧民,利用业余时间用英文撰写了《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》一书,表达对社会的关切。母亲是闻玉梅童年时最崇拜的榜样。
九岁那年,闻玉梅进入一所教会中学读书,那里她总觉得格格不入。衣服大多是姐姐穿旧的,假期时同学们都乘车回家,而她只能挤电车回家。那时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:“我的成绩一定要比他们好!”母亲工作繁忙,陪伴她的时间很少,书籍成了她最好的伙伴。母亲的影响让她从小便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读到白求恩的故事后,她立下志愿:“医学能够直接帮助人们解除痛苦,我将来一定要从事这项有意义的事业。”她的另一位偶像是居里夫人,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了她。从此,她的内心燃起了希望的火焰,家族传承的精神在她血脉中静静流淌。
展开剩余79%1951年,闻玉梅考入上海医学院。一次临床实习经历却让她心情沉重。那时,她遇到了一位怀有二胎的心脏病孕妇。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,但母子终未能保住生命。目睹生命的陨落,闻玉梅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无助,连续数日泪流不止。母亲忧心忡忡地劝她:“你太情绪化了,缺乏冷静和理性,怎么能成为一名好医生?”经过深思熟虑,闻玉梅决定放弃临床工作,转向基础研究,希望从根源解决医学难题。
正当她意气风发准备继续深造时,噩耗传来——母亲突然病逝。悲痛之余,闻玉梅一度想放弃学业,转为助教谋生。关键时刻,姐姐鼓励她:“你热爱读书,无论多难,我们一起扛过去!”给她带来温暖和力量的,还有她的恋人宁寿葆。两人于大学校园相识,医学院的文艺活动中,她弹钢琴,他拉小提琴,慢慢谱写出属于他们的爱情旋律。
1956年,闻玉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学研究生,导师锁定著名教授林飞卿。可当年林教授只招收俄语专业的学生,为了不浪费人才,她将闻玉梅推荐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余教授。那段时间,宁寿葆常从儿科医院匆匆赶来探望她,偷偷塞给她食堂的饭票和菜票,关怀无微不至。
一年后,闻玉梅回到上海医学院担任助教,与林飞卿的师徒缘分得以延续。林教授对她严格要求,做实验时哪怕胳膊稍微抬高一点就要重做,血清稀释时要求每管混匀三次,绝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三年磨一剑,林教授满意地说:“该换导师了!”在其推荐下,闻玉梅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进修,师从微生物学家谢少文教授。谢教授无子,将闻玉梅视如己出,悉心鼓励。她做报告时显得紧张,他轻声安慰:“别怕,我坐你旁边,先让你答,不会的我帮你。”
在三位免疫学大师的指导下,闻玉梅迅速崭露头角。可惜政治风暴打断了她的研究多年。1974年,一纸通知让她重拾希望:“你可以开始肝炎研究了!”当时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,病毒携带率高达10%,甚至她自己班上学生也有7%。这些数字让她下定决心,申请到防疫站学习,从此与乙肝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。
改革开放后,国门逐渐打开。1980年,闻玉梅通过出国进修考试。别人多选长时间项目,她却选择了肝炎研究的三个月短期课程。朋友们觉得可惜,她坚定回应:“我选的是肝炎,不是时间长短!”初到伦敦大学,她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,面对先进设备和技术一时难以适应,感叹差距之大。但她刻苦学习,生活极为节俭,食物只买最便宜的,娱乐活动几乎没有,参观伦敦桥的四英镑门票也舍不得花。三个月学成归国,不仅发表论文,还用省下的钱购置了低温冰箱和幻灯机,这两件设备运回国费用高达90英镑。
她在讲台和实验室里反复强调:“我们一定要摘掉‘肝病大国’的帽子!”1981年,想赴美进修时,已是微生物教研室主任的她被学校难以放行。恩师林飞卿年逾七旬,毅然请缨:“闻玉梅有潜力,这一年主任我来做,她一定要出去!”赴美后,她接触分子病毒学新领域,但实验室认为她不适合高端科研,建议她从事细胞学。闻玉梅不服,报夜校补习,选择学分制课程,必须通过考试,年届47岁的她,白天工作,晚上学习。
考试中,她以黑马姿态让同事刮目相看。远隔重洋,她感激国家的培养,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国家对年轻人的期望,这不仅是金钱投资,更是情感和信任。”两次进修后,她看清差距,回国即搭建进修桥梁,选派学生出国学习,并倡议成立中国首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,立志“造巢引凤”。
长期研究中,她一直思考:未感染者可用疫苗预防,已感染者是否能开发治疗性疫苗,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力控制病毒?国家“863”计划推出后,她及时递交申请。1987年,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正式启动,因无先例,步履维艰。国内缺乏动物模型,国外实验鼠又禁止进口,她几次求助无果。关键时刻,香港一位教授帮助将小鼠进口香港,使她得以“曲线救国”。
路途漫长艰难,但师长们支持不断。1991年,88岁的谢少文教授将协和医科大学赠予他的玉石奔马赠与闻玉梅,赞扬她勤奋刻苦,期望她继续推动中国微生物学事业。林飞卿教授赠送她一把镀金钥匙,寄托“继续开启微生物与免疫学宝库”的厚望。在老师们的激励下,治疗性乙肝疫苗终于诞生。
首次临床试验时,闻玉梅主动报名做志愿者,“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,但不能让别人冒风险。”数周后安全无虞,团队取得阶段性成果。1995年,她在国际权威杂志《柳叶刀》发表论文,首次提出治疗性疫苗的概念,被誉为“治疗性疫苗的先驱者之一”。
科研之路虽漫长,她步履稳健。实验室里一本特别的册子,收藏了无数乙肝患者的来信,记录着他们的痛苦、焦虑与期盼。闻玉梅称之为“人民的期望与重托”。二十余年辛苦耕耘,2009年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。
她感慨道:“虽道路坎坷,但只要目标明确,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。”耄耋之年,闻玉梅的日程依旧满满当当。“我无法与美国同龄人竞争,但我坚信我的学生能做到!”望着一批批学生成为领域翘楚,她心中无比欣慰。实验室研究依旧紧锣密鼓,尽管临近成功,乙肝治愈仍是全球医学难题。
为了实现这个梦想,闻玉梅说:“我绝不放弃,仍将继续努力。”在攻坚乙肝的道路上,她就像那枝红梅,迎雪傲霜,坚韧不拔。
发布于:天津市实盘配资一般不超过多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